更新时间:2025-10-2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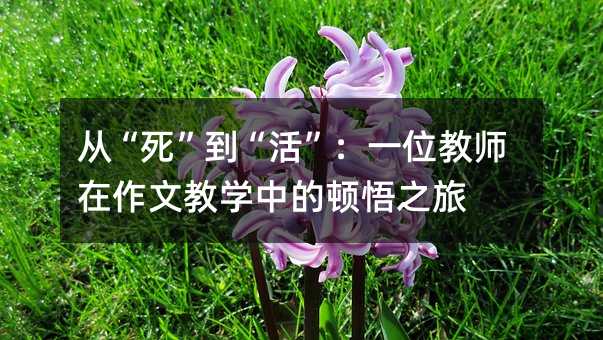
在十月的一个清晨,阳光斜照进进校生化实验室的窗棂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专注气息。我坐在台下,手握笔记本,目光紧锁讲台中央那位正在说话的语文教育专家——袁志勇教授。那一刻,我意识到,这不会是又一场走过场的培训。它更像是一次思想的唤醒,一次对长期困顿于作文教学中的我而言,近乎“点化”的经历。
我教小学语文已有十余年。这些年里,听过不少讲座,翻过无数教学参考书,也尝试过各种所谓的“高效课堂模式”。但大多时候,那些理论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花,看着光亮,却难以渗入日常教学的肌理。直到那天,袁教授用一个半小时,把作文教学从“玄学”拉回了“可操作”的地面。
他的讲座题目是“课堂教学内容有效的思维三段论”。名字听起来学术,可内容却异常清晰、具体。他没有堆砌术语,也没有空谈理念,而是直接抛出三个固定句式,作为学生写作构思的思维支架。这三个句式并不复杂,却像三把钥匙,打开了我长久以来对“如何教作文”的迷思。
第一个句式是:“什么什么样。”
第二个是:“本人、他人、直接事物、间接事物。”
第三个则是贯穿始终的逻辑链条:从现象到本质,从个体到关联。
乍一听,这些似乎过于简单,甚至机械。但袁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不追求花哨的形式,而是直击写作的核心——思维的组织。他指出,很多孩子写不好作文,不是词汇不够,也不是缺乏生活经验,而是脑子里没有清晰的结构。他们知道要写“一次难忘的旅行”,却不知道从何说起,东一榔头西一棒子,最后拼凑成一篇散乱的文字。
而“什么什么样”这个句式,正是为了帮助学生快速锁定描写对象的特征。比如,“那棵树很高大”,“这个玩具很旧”,“妈妈的眼神很温柔”。它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——一个让学生学会观察、学会聚焦的起点。接着,通过“本人、他人、直接事物、间接事物”的分类,引导学生从多个维度去拓展内容。
写“一次考试”,不只是写“我紧张”,还可以写“同桌偷偷递纸条”,写“窗外的风突然停了”,写“老师批改作业时皱起的眉头”。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,恰恰构成了真实感和层次感。
最让我震撼的,是袁教授面对质疑时的回应。有老师提问:“如果所有学生都按同一个句式写,作文岂不是千篇一律?”
袁教授笑了笑,说:“给他一个死的模式,它就是真的死的;可如果给他若干个死的模式,就可以活起来。”
这句话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脑海中的迷雾。
我们总害怕“套路”,怕学生被框住,怕创造力被扼杀。但我们忘了,创造力不是凭空蹦出来的,它需要依托。就像学书法,先临帖,再创作;学音乐,先练指法,再即兴演奏。写作也一样。一个孩子连最基本的表达结构都没有掌握,谈何创新?所谓的“自由表达”,往往只是混乱的代名词。
袁教授所说的“死”,其实是“规范”;而“活”,则是“迁移与融合”。当学生掌握了多个“死”的结构——比如时间顺序、因果关系、对比描写、心理变化——他们自然会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调用,组合出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这才是真正的“活”。
他讲了一个故事,叫《聪明的屠夫》。说的是一个屠夫杀牛,别人问他为什么刀法如此精准,他说:“我看到的不是整头牛,而是牛的关节缝隙。”
袁教授说,教学也该如此。我们要教会学生“看见缝隙”——那些隐藏在生活表象下的逻辑关系、情感变化和因果链条。作文不是堆砌事件,而是揭示联系。
另一个故事是《三头牛的尾巴》。三头牛并排站着,一个孩子说:“它们的尾巴都在动。”老师问:“为什么动?”孩子说:“因为有苍蝇。”老师再问:“那为什么一头动得多,一头动得少?”孩子开始观察,发现有的牛皮肤紧,有的松,有的在吃草,有的在休息。
于是,原本一句平淡的“尾巴在动”,变成了有细节、有分析、有判断的描写。
这让我想到我的学生。他们写“妈妈做饭”,往往只写“妈妈在炒菜,香味飘出来”。但如果用上“间接事物”的视角,就可以写“锅铲碰撞的声音惊醒了午睡的猫”,或者“油星溅到围裙上,留下几个褐色的小点”。这些细节不是编造,而是观察的结果。而观察,是可以被训练的。
袁教授还打了个有趣的比喻:自学成才的学生,像打麻将里的“自摸和”;老师教会的学生,是“碰和”。他说,我们做老师的,就是要让学生“碰和”。不是贬低自学者,而是强调教学的价值——教师的存在,是为了加速学生的认知进程,让他们少走弯路,更快地抵达理解的彼岸。
这个比喻让我笑了,也让我沉思。的确,有些孩子天生敏感,能从生活中自然汲取写作养分。但大多数孩子不是这样。他们需要被“碰”一下,被点拨一下,被结构化地引导一下。否则,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停留在“我写不出来”的焦虑中。
那天的讲座结束后,我走在回校的路上,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三个句式。我突然意识到,这些句式不只是教作文的工具,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传递。它教会学生如何从混沌中提取秩序,如何从碎片中构建整体,如何从“看到”走向“想到”。
于是,我在接下来的作文课上,尝试引入“思维三段论”。第一节课,我让学生写“一件让我生气的事”。以往,他们往往直接进入叙述:“同桌拿了我的笔,我很生气。”然后就卡住了。这次,我先让他们用“什么什么样”描述当时的场景:“他的手突然伸过来”,“笔帽掉在了地上”,“他的表情有点心虚”。
接着,引导他们从“本人、他人、直接事物、间接事物”四个角度补充细节:我握紧了拳头(本人),他低着头不敢看我(他人),桌角的橡皮被碰掉了(直接事物),窗外的鸟突然飞走了(间接事物)。最后,让他们思考:这件事背后,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?比如,他是不是最近总忘带文具?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?
一节课下来,学生交上来的文字明显不一样了。不再是流水账,而是有了温度、有了层次、有了思考。有个孩子写道:“原来我生气,不只是因为笔被拿走,而是觉得不被尊重。可后来我想,也许他真的忘了带,而不是故意的。”—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记叙,而是初步的反思。
这让我更加确信,作文教学的本质,不是教孩子“写得漂亮”,而是教他们“想得清楚”。语言是思维的外壳。当思维有了骨架,文字自然会站立起来。
当然,我也遇到过挑战。有家长问我:“这样教,会不会限制孩子的想象力?”
我的回答是:想象力不需要无序的自由,它需要落地的支点。就像风筝,飞得再高,也得有根线。那根线,就是清晰的思维结构。没有它,风筝只会乱撞,最终坠落。
还有老师担心:“这样教,会不会让课堂变得机械?”
我想说,工具本身是中性的。关键在于怎么用。如果只是让学生机械套用句式,那确实会僵化。但如果把句式当作思维的脚手架,随着学生能力提升逐步拆除,它就能完成它的使命。
袁教授的讲座,最打动我的,是他对教学的“实”与“深”的平衡。他不追求表面的热闹,也不沉迷理论的玄妙,而是扎扎实实地给出可操作的方法。同时,这些方法背后,又藏着对认知规律的深刻理解。他知道孩子在什么阶段需要什么,也知道教师在教学中常陷于哪些误区。
比如,我们常常急于让学生“升华主题”,一写母爱就要“伟大”,一写老师就要“无私”。结果,情感被拔高,变得虚假。袁教授的做法相反:他让学生先沉下去,写具体,写真实。情感自然会从细节中浮现。就像他讲的《鹦鹉的故事》:一只鹦鹉总学人说话,主人嫌它吵,把它关进笼子。
后来主人病了,鹦鹉不再说话,只是每天盯着门口,等人来。有一天,医生来了,它突然喊:“快救救他!”——那一刻,情感才真正击中人心。
写作的力量,从来不在口号里,而在细节中。
现在,每当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学生们低头写作的样子,我总会想起那天生化实验室里的阳光。它不刺眼,却足够明亮,照亮了某个长久被忽略的角落。袁教授没有给我一堆新名词,但他给了我一种新的眼光——看作文,看教学,看孩子。
教育不是一场华丽的表演,而是一次次微小的点燃。我们不需要每节课都惊天动地,只要能让一个孩子在某个瞬间,突然明白“原来可以这样写”,就够了。
而这一切,始于几个“死”的句式,终于无数个“活”的表达。
写作如此,思维如此,成长亦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