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教下乡:语文课堂在山野间绽放
【来源:易教网 更新时间:2025-11-19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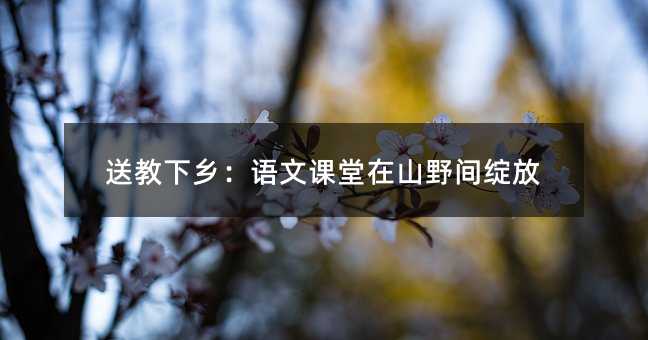
三月的清晨,薄雾还缠绕在武隆的山坳里,一辆小车碾过蜿蜒的土路,载着几位小学语文老师驶向最偏远的青龙小学。车窗外,油菜花黄得晃眼,孩子们的笑声从校门口传来——这是一场用真心焐热课堂的旅程。
去年冬天,县教科所肖素碧老师在重庆参加教研培训时,和专家们聊到乡村教育的困顿:孩子们捧着课本,却读不出文字里的温度。回来后,她召集县小语会成员开了场“头脑风暴会”。会议室里,茶水凉了又续,大家反复琢磨着“送教团”“送教组”“送教小分队”几个名字,最后,一句“我们能为武隆小语做点什么”成了定音锤。
于是,“武隆县小学语文送教队”应运而生。
四月的花香还没散尽,县教委会议室里,冉建容副所长宣布了这个团队的正式成立。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一句朴实的话:我们手牵手,一起把语文的种子种进山里的土壤。
送教队的三重使命,说白了就是三句大实话:先带出一批能扛事儿的骨干教师,再让这些老师像蒲公英一样,把好方法播撒到全县的课堂,最后用二到三年时间,把全县小学语文的“根”扎得更深——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看见春天。
真正让课堂活起来的,是那些“不按常理出牌”的瞬间。去年秋,送教队员李芳去到海拔800米的龙坪小学。那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,她没用PPT,只带了十张手绘的卡片:小蝌蚪、青蛙妈妈、水草、石头……孩子们围坐一圈,跟着她比划着“黑黑的脑袋,长长的尾巴”,教室里突然响起一片“咯咯”笑。
课后,一个叫小雨的女生攥着她的衣角问:“老师,小蝌蚪最后找到妈妈了吗?”李芳蹲下来,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:“找到了,就像你找到妈妈一样。”小雨眼睛亮了,小声说:“我以后也想当老师,教大家认字。”
这样的故事在送教队里早不是个例。队员张明在偏远的白果小学发现,孩子们对“比喻句”总犯迷糊。他没讲定义,而是带着孩子们去操场看“云朵”。他说:“看,云朵像不像棉花糖?这就是比喻呀!”孩子们跑着喊:“老师,云朵是棉花糖,我的书包是小马!”——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符号,成了他们指尖的风、脚下的路。
送教队的“魔力”,还藏在那些“意外收获”里。一次去羊角小学,队员王静发现孩子们的朗读声轻得像蚊子哼。她没急着纠正,而是带他们读《春晓》: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”她故意把“闻”字拖长,让孩子们学着鸟叫。孩子们从“叽叽喳喳”到“唧唧啾啾”,最后竟自发编起小诗:“风儿吹,草儿摇,小雨点,跳跳跳。
”朗读课变成了游戏,王静笑着拍手:“原来语文,可以这么好玩。”
为什么送教队能扎下根?因为每个老师都明白,乡村课堂需要‘看见’。武隆的山路弯得像语文书里的“曲折”,但老师们总说:“走慢点,别急着赶路,孩子们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陪。
”他们带去的不是教案,是带着温度的“活方法”:用本地故事教写作,用山歌教韵律,甚至把田埂当课堂——“看,这棵老槐树,像不像爷爷的白胡子?”孩子们笑着点头,作文本上便多了“爷爷的白胡子”这样的句子。
更难得的是,送教队从不“一送了之”。每次活动后,他们都会和乡村教师一起备课。在双河小学,老教师陈老师第一次用“角色扮演”教《司马光》,课后她拉着队员的手说:“以前我总怕讲得不好,现在知道,语文是教人‘看见’。”如今,陈老师成了校内“小老师”,带着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备课。
送教队的辐射效应,就这样悄悄生长。
如今,送教队已走过四季。山里的孩子读起《静夜思》,会指着月亮说:“老师,这月光像外婆的银镯子。”语文课是他们和山野、和家人、和自己对话的桥梁。武隆县的小语会成员们常聚在茶馆,聊起最近的送教点:“今天在火炉小学,孩子们用‘像’字造句,说‘爸爸的背像山’,我眼眶就热了。”
送教下乡的路,没有终点。它只是让语文的种子,在山野间悄悄发芽。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读出“春眠不觉晓”,当乡村教师在备课本上写下“原来语文可以这样教”,教育的光靠一次次弯腰、一句句“我们试试看”照进每个角落。山风掠过田野,语文课的笑声,正随着新芽一起生长。
 搜索教员
搜索教员

最新文章

热门文章
- 何教员 西安汽车大学 汽车工程
- 潘教员 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 消防工程
- 马教员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
- 郭教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工程(大一英语专业)
- 徐教员 北方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
- 陈教员 北京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
- 刘教员 太原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
- 周教员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
- 郝教员 华北电力大学(北京) 英语能源专业
- 戴教员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