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语文的土壤里种下智慧的种子:一位教师的深度教学手记
【来源:易教网 更新时间:2025-09-10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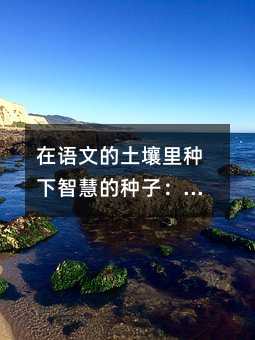
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洒进教室,三年级的孩子们正捧着语文课本,一字一句地朗读着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。声音稚嫩,却带着一种奇特的专注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,他们读的不只是文字,而是一个正在悄然展开的世界。
我们常常把语文课简化成“识字、朗读、背诵、默写”的流程,仿佛只要完成这些步骤,孩子就掌握了语文。但真的是这样吗?当一个孩子能准确默写出“蝌蚪”两个字,却不知道池塘里那些黑点点就是小蝌蚪的前身;当他能流畅背诵《咏鹅》,却从未见过一只真正的白鹅在水面上划动红掌——我们真的完成了语文教育吗?
苏霍姆林斯基曾说:“人才只靠人才去培养,能力只能靠能力去培养,才干只有靠才干去培养。”这句话在我执教的第十个年头,终于显露出它沉甸甸的分量。它不是在强调教师的权威,而是在提醒我们:教育的本质,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唤醒。你无法用枯竭的心灵去点燃另一颗灵魂的火种。
如果你自己对文字没有感动,又怎能期待孩子被《秋天的雨》打动?如果你从未在某个清晨为一句诗驻足,又怎能引导孩子体会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微妙?
现在的教材,确实像一片浩瀚的海洋。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的科普短文,从民间故事到儿童诗,内容包罗万象。这本是好事,但若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“讲完”课文,那再丰富的文本也只是被切割成知识点的碎片。
我曾见过不少教案,把一篇充满童趣的童话拆解成“生字几个、近义词几个、中心思想几句话”,仿佛语文是一道可以套用公式的数学题。结果呢?孩子学会了答题,却失去了对故事本身的兴趣。
我开始尝试改变。教《我是什么》这篇课文时,我没有急着让学生划出生字词,而是先问:“你们有没有想过,自己到底是什么?”孩子们愣住了。一个孩子小声说:“我是我啊。”我笑了:“对,你是你。但‘我’也可以是很多东西。
比如,我有时候是天上的云,有时候是地上的水,有时候钻进你们的杯子里,有时候又躲在冰棍里——猜猜我是谁?”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当他们终于猜出“水”时,眼睛都亮了。那一刻,他们不是在学课文,而是在参与一场关于自我与自然的哲学游戏。
这种“慢下来”的教学,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孩子们开始主动提问:“老师,‘融化’和‘溶化’有什么不一样?”“为什么说‘灌溉田地’,不说‘浇灌田地’?”这些问题,过去在赶进度的课堂上根本不会出现。它们来自真实的困惑,来自对语言的敏感。我意识到,语文的根基,从来不是标准答案,而是好奇心。
于是,我把更多时间用在“无用之事”上。比如,带学生去校园里找“带‘氵’的字”——他们在水龙头、鱼池、雨后的水洼边发现这个偏旁的踪迹;比如,让学生用身体表演“波纹”“跳跃”“奔跑”,感受动词的力量;比如,读完《植物妈妈有办法》后,我们真的去采集蒲公英,对着它吹气,看种子如何乘风飞翔。
这些活动不会直接提高考试分数,但它们让文字从纸上站了起来,走进了孩子的呼吸与动作里。
有一次,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孩在日记里写道:“今天我变成了一滴水。我从云里跳下来,落在小草的头上,它抖了抖,我就滑到泥土里。我钻啊钻,看见蚯蚓在挖隧道,它请我喝了一口茶——原来是地下的泉水。”我读着读着,眼眶热了。这不是在写作文,这是在用语言创造生命。而这种创造,恰恰是语文最珍贵的部分。
当然,基本功依然重要。识字、写字、朗读,这些是语文的“骨架”。但我逐渐明白,骨架必须有血肉才能站立。一个孩子写“游”字,如果只是机械地记住“左中右结构,三点水,方,子,人”,他可能会写错。
但如果他先在泳池里扑腾过,感受过水从指缝流走的触感,理解“人”在“方”(象征泳道)中带着“子”(象征孩子)在水(氵)中移动——这个字就活了。它不再是一堆笔画,而是一段经验的凝结。
这也让我重新思考“学者型教师”的含义。它不是要求我们成为百科全书,而是保持一种永不枯竭的求知欲。当孩子问“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”,我不会说“下课查查资料”,而是和他们一起做三棱镜实验,看阳光如何被分解。当他们对古诗中的“舴艋舟”好奇,我会找来古代小船的图片,甚至用纸折一只,放在水盆里演示。
我的知识储备或许有限,但我的探索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教育。
家庭教育同样如此。很多家长焦虑地问我:“在家怎么辅导孩子语文?”我总是反问:“你们一起读过故事吗?读完后聊过吗?孩子问‘为什么’的时候,你是回答‘书上不是写了’,还是和他一起找答案?”语文能力的生长,始于家庭中那些看似随意的对话。
当父亲指着晚霞说“这颜色像不像火烧云”,当母亲在煮汤圆时说“你看,它们从沉底到浮上来,就像学会了游泳”,这些时刻,语言与生活完成了最自然的融合。
我见过一位母亲的做法让我深受触动。她女儿读《树之歌》时,对“榕树”感到陌生。这位母亲没有上网搜图片,而是周末带孩子去公园,找到一棵大榕树,让孩子摸树皮、看气根、数枝条。回家后,孩子主动画了一幅画,题为《我和榕树的秘密》。这种学习,深植于感官与情感,远比背诵十遍课文更有效。
技术的发展也让语文学习有了新的可能。现在的孩子能轻松看到世界各地的影像,听到各种方言的朗读。我鼓励学生录制自己的课文朗读,配上简单的背景音乐,分享给同学。一个口吃的孩子,为了录好《小英雄雨来》,反复练习了二十多遍,最终不仅读得流畅,还在班上获得了热烈掌声。技术在这里不是替代,而是放大了表达的勇气。
但无论如何创新,语文的核心始终未变:它是关于理解与表达的学问。理解世界,理解他人,理解自己;表达观察,表达情感,表达思想。小学三年级,正是这个能力萌发的关键期。他们的语言还稚嫩,思维还具体,但已经能感受到文字的温度。一篇课文,可以是一扇窗,让他们看见更广阔的生活;也可以是一面镜子,照见自己的内心。
记得教《荷花》一课时,朱自清写“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”。我问:“为什么用‘冒’,不用‘长’或‘开’?”孩子们讨论了很久。一个男孩说:“‘冒’字让我觉得荷花很着急,它等不及了,‘噗’地一下就钻出来了!”全班都笑了,但笑完后陷入了沉思。这就是语言的魅力——一个字,能唤醒一千种想象。
作为教师,我的任务不是把标准答案塞进他们的脑袋,而是守护这种想象的火花。当孩子说“我觉得春风是绿色的”,我不纠正“春风没有颜色”,而是问:“为什么你觉得是绿色的?你能画出来吗?”因为我知道,在语文的世界里,逻辑的边界之外,还有更广阔的诗意空间。
教育不是填充容器,而是点燃火焰。在语文的课堂上,我们种下的不是知识点,而是对世界的好奇,对语言的敏感,对美的感知。
这些种子或许不会立刻发芽,但总有一天,当他们在某个黄昏突然想起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的句子,当他们用文字安慰一个伤心的朋友,当他们写出第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诗——那时,他们会记得,曾有一位老师,允许他们慢下来,去触摸文字的温度。
而这,就是语文教育最深的回响。
 搜索教员
搜索教员

最新文章

热门文章
- 胡教员 福建医科大学 五年制临床医学
- 刘教员 首都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
- 姜教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金融
- 夏教员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会计学
- zl教员 北京工业大学 凝聚态物理
- 黄教员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(机器人)
- 张教员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
- 张教员 北京邮电大学 电信工程及管理
- 杨教员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
- 吴教员 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