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的重量:一个边疆孩子的语文课
【来源:易教网 更新时间:2025-10-09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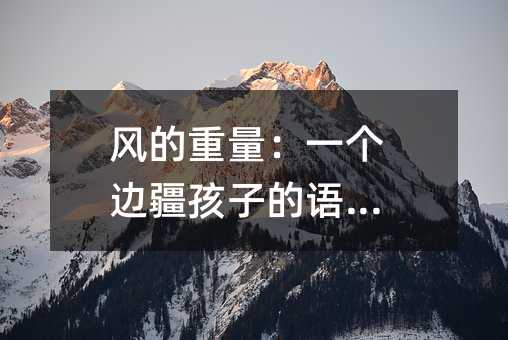
荒茫茫的戈壁滩上,风从西边刮过来,不是吹,是推。它撞在土坯墙上,咣咣当当地响,像一辆老式拖拉机在夜里抛锚,气缸里还卡着半块没烧尽的柴火。我蹲在教室后头,手里攥着那本卷了边的语文课本,纸页泛黄,墨迹被汗浸得模糊,像被沙尘暴舔过一遍的碑文。老师说,预习是“摸黑走路前先伸手探路”。可我哪有灯?
只有风,嗖嗖地从窗缝钻进来,把讲台上的粉笔灰卷成细小的漩涡,打在我脚踝上,凉得像谁悄悄往衣领里塞了一颗玛瑙般的石子。
那年冬天,我第一次在晚自习时把《背影》读出声来。声音卡在喉咙里,像被冻住的井水。前排的马小兰转过头,眼珠子亮得像刚从沙堆里挖出来的铜镜。“你念得像哭丧。”她说。我没答话,继续念。父亲买橘子那段,字句笨重,却沉得压手。
我忽然想起我爸——他去年冬天去矿上拉煤,凌晨四点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三轮车出门,车斗上绑着两袋面粉,后座捆着我的课本。他没回头,只在院门口停了三秒,风把他的围巾吹得像一面残破的旗。我那时不懂什么叫“蹒跚”,可我知道,那车轮碾过冰碴的声音,比任何注释都更接近文字的骨头。
课堂上,老师讲修辞,说比喻是“让抽象的东西有体温”。可我们这儿没有抽象。风压得很硬,能割开棉袄;沙粒打在脸上,不是痒,是疼。我记笔记,用铅笔,因为圆珠笔一冷就凝住,像冻僵的虫子。我在“借景抒情”四个字下面画了条歪斜的线,旁边写:“风不是风,是大地的文法。”没人懂。
但我知道,当夕阳把沙丘染成赭红,当乌鸦从枯柳上惊起,扑棱棱飞向天边,那不是风景,那是语言在呼吸。我偷偷抄下课文里所有带“月”字的句子——“举头望明月”“月是故乡明”——不是为了背,是为了在夜里抬头时,能确认头顶那片天,和爸爸拉煤时走过的,是同一片。
课后复习,我总去村口那座废弃的砖窑。那里没电,没暖气,但风安静些。我把课本摊在膝盖上,用冻得发紫的手指一页页翻,像翻一块块晒干的羊皮。有时风突然停了,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,像鼓槌敲在空铁桶上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老师说“温故而知新”不是重复,是重新认识。
那些字,那些句,不是刻在纸上,是刻在风里,刻在冻裂的土墙缝里,刻在母亲半夜起身给我掖被角时,呵出的那团白雾里。
我不再边看电视边写作业。电视里的人笑得太大声,吵得我耳朵里嗡嗡响,像一群蜜蜂在脑壳里筑巢。我搬了张小凳,坐在灶台旁,借着炉火微光写字。火苗跳动,影子在墙上乱晃,像一群没学会走路的汉字。母亲在锅里煮土豆,蒸汽升起来,模糊了窗玻璃。
她不说话,只是偶尔往我碗里添一勺汤,油花浮在上面,像一小片被风吹皱的月亮。我写完作文,题目是《我最怕的季节》,交上去后,老师在批语里写:“有血有肉。”我没告诉别人,那篇文章里写的“怕”,不是寒冷,是看见父亲脱下棉鞋,脚趾缝里嵌着黑泥,像被大地咬了一口。
考试那天,风又来了。卷子发下来,墨迹被风吹得微微发颤。我盯着最后一道题:“请结合生活实际,谈谈你对‘孝’的理解。”我搁下笔,望向窗外。远处,一辆运煤车正缓缓驶过,车轮压过结冰的路面,发出沉闷的咯吱声。我想起我爸,想起他总在饭桌上把肉夹到我碗里,自己只吃咸菜。他从不说“爱”,也不说“责任”。
他只是在每个清晨,把我的书包挂在车把上,像挂一件不能丢的家当。我提笔写下:“孝,是风停的时候,你仍记得有人为你留着一盏灯。”没写完,铃响了。卷子交上去,没人问我写的是不是标准答案。但我知道,那不是考试,是心在说话。
后来我常去河边捡石头。河床干了,露出大片龟裂的泥土,石头躺在那儿,被水流磨得圆润,又被风沙磨出棱角。我挑出几颗颜色最斑斓的,揣进兜里,带回教室,压在语文书里。它们不值钱,但它们记得水怎么流,风怎么吹,太阳怎么把它们烤热,又怎么在夜里把温度一点点抽走。
就像那些课文,那些句子,不是用来背的,是用来活的。当你在寒夜里听见风穿过屋檐的呜咽,当你在沙尘暴中眯着眼睛认出远方的路标,你就懂了——语文不是课本,是大地的文法,是风的重量,是你在荒原上走了一千公里,终于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。
我依然在晚自习后多读半小时《城南旧事》。林海音写“爸爸的花儿落了”,我写“爸爸的棉袄破了”。她写童年,我写生存。她用温柔,我用沉默。可我们都一样,在风里,用文字搭一座不倒的屋。
风又起了。它从祁连山那边翻过来,卷着沙,卷着碎冰,卷着某个孩子未寄出的信。它不问你懂不懂修辞,它只问: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,为一句诗,流过泪?
 搜索教员
搜索教员

最新文章

热门文章
- 陈教员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
- 李老师 中学高级教师 化学
- 李教员 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 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类
- 周老师 大学讲师 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类
- 王教员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
- 付教员 北京师范大学 英语
- 郑教员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
- 崔教员 北京工业大学 光学工程
- 蔡教员 北京物资学院 商务英语
- 禹教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