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时间:2025-10-14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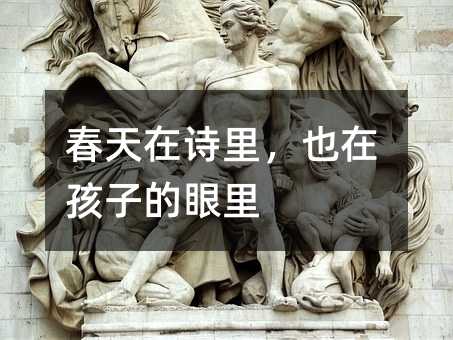
二年级的孩子,刚学会用拼音拼出“柳”字,还没完全搞懂“似”和“像”有什么区别,却已经在晨读时把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念得清脆响亮。他们不是在背诗,是在用声音摸春天。
教室窗外的柳枝,前几天还干巴巴地垂着,今天却悄悄冒出了嫩黄的小芽。孩子们指着它喊:“老师,你看,是不是诗里说的那样?”我不用解释“拟人”或“比喻”,他们自己已经把诗和眼前的树连在了一起。这比任何课件都真实。
那天我拿出两首诗,《咏柳》和《春日》,没讲作者,没讲背景,只问:“这两首诗,都写了什么?”一个男孩举手:“都说了风。”另一个女孩接:“都说了颜色,绿的,红的。”第三个孩子小声说:“它们都在夸春天。”没人说“赞美”,但他们的意思,比教参上的定义更准。
《咏柳》像一支铅笔,一笔一笔,描出柳条的细长,描出叶子的嫩绿,描出风怎么把叶子剪得整整齐齐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孩子们读到这里,有人模仿剪刀的手势,有人轻轻吹气, pretend自己是春风。他们不是在理解诗句,是在用身体演诗。
《春日》不一样。它像一桶打翻的颜料。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没有具体哪棵树,没有哪朵花,全是大片大片的色彩在流动。一个孩子说:“这首诗像我奶奶家的菜园子,春天一来,啥花都冒出来了。”另一个说:“它不像《咏柳》那样盯着一棵树,它是把整个春天抱在怀里。”
我把两首诗并排写在黑板上,不分析修辞,不讲格律,只让他们轮流读,读完后闭上眼睛,问:“你眼前有什么?”有人画出柳树,有人画出满地野花,有人画出风在跑,有人画出太阳在笑。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真实的画面。
后来我带他们到校园里走了一圈。不带笔记本,不带任务,只问:“你闻到了什么?”“你听到了什么?”“你看到哪一处,觉得像诗里写的?”一个女孩蹲在墙角,指着一簇蒲公英:“这像不像‘万紫千红’?它不是花,但风一吹,就飞满了天。”我没想到,她用的词,和朱自清笔下“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”是一样的感觉。
我们没读《春》这篇散文,但孩子们自己说出了它的味道。他们不需要知道朱自清是谁,不需要知道什么是“散文”,他们只是觉得,春天来了,心里暖暖的,想说点什么。而诗,刚好替他们说了。
有孩子回家后,把《咏柳》画成一张卡片,贴在冰箱上。妈妈说,他每天早上吃饭前都要念一遍。有个爸爸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段视频:孩子站在阳台上,对着楼下刚发芽的梧桐树背《春日》,背到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时,突然停下,指着树杈上一只麻雀说:“它也是春天的一部分。”
教育不是灌输,是唤醒。我们以为孩子不懂古诗,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懂春天。他们不关心“七言绝句”是什么结构,但他们知道,风不是冷的,是带着味道的;柳条不是树,是春天的手指;花不是开在土里,是开在心里。
我见过太多课堂,老师拿着PPT讲“借景抒情”,讲“象征手法”,讲“诗人情感”,学生却一脸茫然。诗,不是用来分析的,是用来生活的。当孩子能指着一片叶子说“这是剪刀裁的”,当他们能蹲在草丛里数出五种不同的绿,诗才真正活了。
我们总想教孩子“读懂”古诗,却忘了,古诗本来就是孩子写的。古人写诗,不是为了考试,是为了表达看见春天时那一声轻轻的“啊”。我们今天教诗,也不该是为了让他们在试卷上填对“修辞手法”,而是让他们在某个清晨,突然停下脚步,说:“今天风真像剪刀。”
春天不会等我们备好课才来。它在柳枝上,在泥土里,在孩子仰起的小脸上。我们能做的,只是把诗轻轻放在他们手边,然后退后一步,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去触摸它,去拥抱它。
有天放学,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孩子,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。上面歪歪扭扭写着:“春风不是剪刀,是妈妈的手,帮我把冬天的被子掀开。”
我没改错字,也没加评语。我只是把纸条夹进了教案本里。
那一页,比所有教学反思都重。